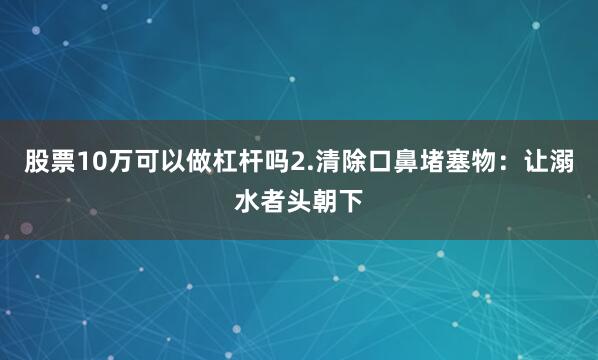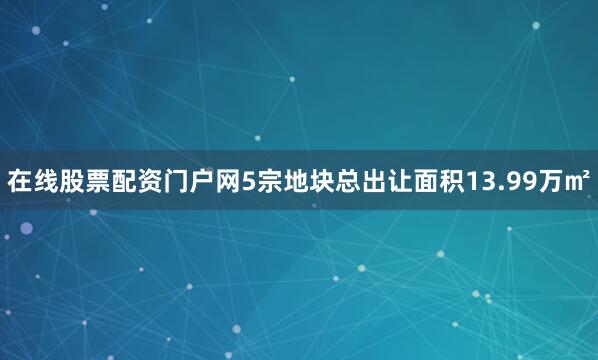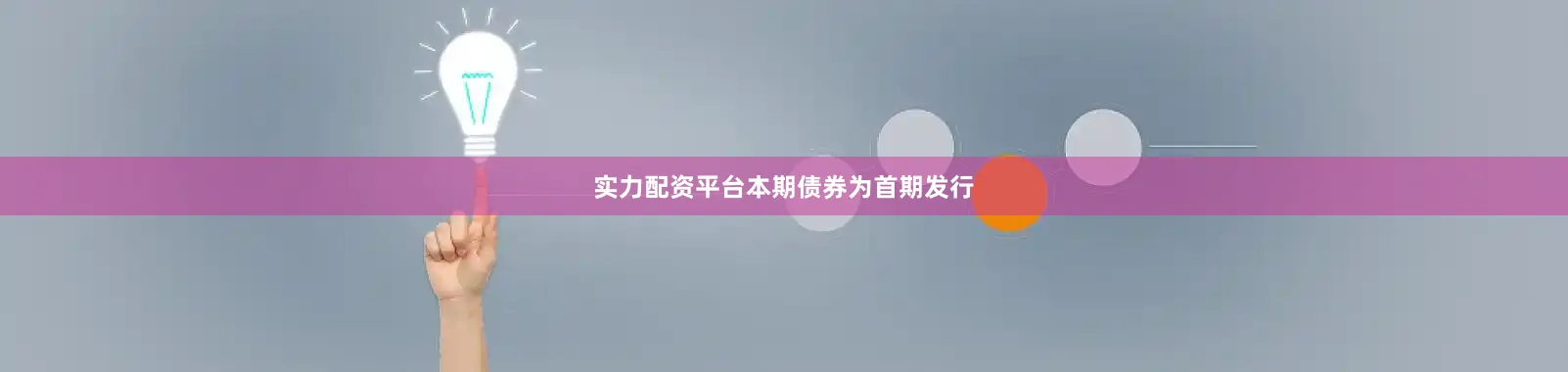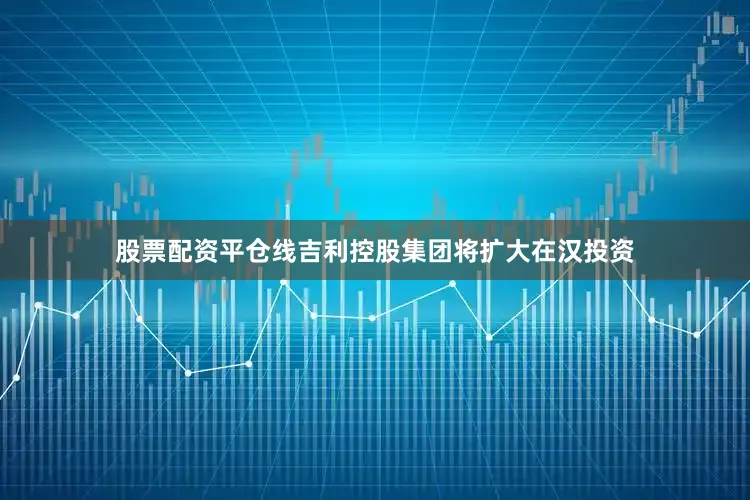这一季的《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》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播出后,总会有人质疑:
这还能笑吗?房主任的经历让你笑了;陈艾谈精神健康问题时,你也笑了。观众怎么如此冷漠?这还是喜剧吗?
有些人对“笑”理解得过于简单,仿佛笑就是轻浮、就是对事不负责的表现。
这种想法,正是典型的“伪严肃”心态——我站在道德高地,告诉你这可以笑,那不能笑。
精神健康问题不能笑,女性的苦难不能笑,性别冲突不能笑,阶层问题更是禁忌。
难道一些观众以为单口喜剧演员只是来“展示自己有多惨”的吗?
看演员谈论精神健康、月经、痛苦,台下响起的笑声,你会觉得不对劲。
但你有没有思考过——笑,未必是嘲笑痛苦,恰恰可能是观众发现:
“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。”
对于这些人,我理解他们内心想表达的东西。但与此同时,一个问题在我脑中浮现,我忍不住想反问:
“如果你看单口喜剧只关心好不好笑,那和挠自己的胳肢窝有什么区别?这种审美标准,未免太低了吧。”
展开剩余82%很多人对单口喜剧的期待,似乎还停留在“消遣娱乐”阶段。一个段子响了,就觉得值得;如果没有反应,演员就被认为“不好笑”。
这种评判标准简单直接,却忽略了单口喜剧最吸引人的地方——文本的智慧与勇于冒犯的精神。
正如我提到的,房主任和陈艾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“精彩”,绝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制造了笑点。
房主任通过坦诚而接近残酷的方式,讲述她的“浴火重生”经历,把生活中的痛苦、人性的脆弱,甚至死亡的阴影,一一展现给观众。
我们笑,不仅是因为她的生命力和自嘲精神,更因为从她的故事中,我们看到的是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坚韧与脆弱。
而当另一位演员谈到精神困境时,观众的笑声,难道真的是在嘲笑一个病人的痛苦?
我想,正好相反。
这笑声里包含着无数复杂的情感:有“我并不孤单”的释然,有“她能把这件事讲得如此幽默”的惊讶,还有“终于有人敢揭开这个话题”的敬佩。
这是一种深刻的共情。喜剧演员像外科医生,手持“幽默”这把刀,精准地切开我们不敢触及的伤口。
她的“技巧”在于,她能精准找到痛苦与荒诞之间的联系,用冒犯的姿态打破沉默的禁忌。
观众的笑,是对这精湛“手术”的最佳反馈。我们并非在笑病痛本身,而是在笑她如何巧妙地解构痛苦,用智慧战胜困境。
如果简单粗暴地将观众的笑声视为“对苦难的漠视”或“人性的堕落”,这不仅是逻辑的懒惰,更是对喜剧创作规律和观众智慧的极大侮辱。
我一直觉得很奇怪——单口喜剧在国内被称为“脱口秀”已经第七年了(我指的是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一季算起的七年,不是地下演员的演出年限),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,依然从“我好不好笑”出发来观看,而不是从文本本身去欣赏?
有些单口作品的艺术价值,已经接近甚至不亚于一篇文学作品了。
当然,我懒得举例,不是没有例子,而是真的不想花力气分析文本,我又不是老师,只是一个普通观众,不想上课!
但有时我在想,那些仅从“我笑了没”出发的人,是不是从未经历过这些事?或者根本不愿意面对、不愿意承认这些现实存在?他们是不是在逃避——“我没遭遇过,关我什么事?”“我不懂,不想懂,你讲得再苦,我也不高兴。”
前几天,我看到一篇文章,突然让我对“脱口秀”有了新的理解——
原来,国内真正意义上的脱口秀,是指互动式脱口秀。台上的演员不需要写完整的剧本,靠即兴表演、观众的互动、气氛调动,娱乐性更强,受众也广泛。
而我们平时看到的视频平台上的“脱口秀”节目,更准确的说法是“单口喜剧”。演员们将剧本写得一字一句,每一段都是结构完整、节奏紧凑的独立作品,只是借用了“脱口秀”这一标签来传播。
所以,如果你仅仅是想要“笑”,那就去看互动式脱口秀吧。
而如果你觉得“笑不出来”,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对“冒犯”的恐惧,和被过度消费的“共情”。
这恰恰是艺术最需要警惕的陷阱。
真正的艺术,永远不会为了让你舒服。它的目的是挑战你、冒犯你,让你在原有的认知框架上裂开一道口子,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。单口喜剧,正是通过笑声完成这一过程。
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这篇文章“说教味”过浓,觉得我像是在摆知识谱,讲什么“你们不懂单口”或“你们怎么不笑”。
但我要说,我当然明白,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单口喜剧和脱口秀的区别,我也从来没有强迫别人去笑。
我只是一个早期开始观看的观众。
2017年,我曾在开放麦现场看到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二季冠军的练习演出。
那一刻,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,但他的表演太精彩了,无法用言语形容。
原本是为了庞博去的,却没想到竟然拍了他更多的照片。
我没有想到,后来还能看到三遍他的完整演出,还不算上刷短视频时看到他的片段——第一次是在开放麦,第二次是在《脱口秀大会》现场,第三次是在电视上看他的正式演出。
如果你愿意,我可以再浪费一分钟陪你。
发布于:福建省云南配资公司,股市如何配资炒股,杠杆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